破局与重构 朱熹同安县学革新范式
□洪瑜瑛
南宋绍兴二十三年(1153年),年仅24岁的朱熹赴任泉州同安县主簿。当他踏入这座闽南海滨小城时,触目所及是一派斯文零落之象:学宫倾圮,斋舍凋敝;典籍蒙尘,虫蛀鼠啮;学规废弛,诵读不闻;士子汲汲,唯务利禄;前贤遗风,湮没无闻。不过,这并未吓倒这位年轻的官员,反而使其胸中激荡起一股“救斯文于不坠”的使命感。
同安作为朱熹理学思想的“实践原点”,其实体空间和精神象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。朱熹在同安开创的教育实践,标志着朱熹教育范式的雏形形成,重塑了同安地域的文化基因,为后来朱子书院的创立奠定基石,更奠定了一套影响中国乃至东亚书院近千年的教育范式。
同安县学是朱熹教育思想的第一片“试验田”。在同安四载,朱熹以“为己之学”为灵魂,进行了一场深刻的儒学教育革新,重建了学问的价值坐标。
空间重塑与理念奠基。针对县学场所残缺、功能紊乱之问题,朱熹首先倾力翻新学殿、讲舍、斋居,提升教育环境。其中,同安县学原有四斋(学舍),一度被裁减为两斋。朱熹恢复四斋制,并将原斋名“彚征”改为“志道、据德、依仁、游艺”。“彚征”源于《易经》“君子以彚征”,朱熹认为该斋名存在以“利禄诱人”之嫌,便以《论语·述而》中孔子所言“志于道,据于德,依于仁,游于艺”重新命名四斋。
这四个名称指向儒学教育的四个核心目标:道德修养、德行实践、仁心培育和技艺掌握。体现了朱熹对同安学子的深切期许。他从空间重构及命名细节入手,批判功利性学习,强调以德行涵养为基础的“为己之学”。
典籍抢救与文脉筑基。朱熹接手同安县学时,面对的是一幅文化凋零的景象:官藏典籍仅有一柜,且无籍可查、管理混乱。当他打开尘封的书柜,眼前是“故敝残脱,无复次第”的惨状,珍贵无比的教学资源“与埃尘虫鼠共敝于故箱败箧之间”,以致濒临“泯泯无余”的境地。朱熹痛心疾呼:“其亦不仁也哉!”
针对县学典籍残破散佚、管理失序之现状,朱熹立即展开系统性抢救,从书柜中整理出6种191卷虽残破但尚可阅读的书籍。同时,创新性地“下书募民间”,成功从民间征集回散佚的典籍2种36卷,使官方藏书与民间资源有效联结,拓宽文化积累之源头。接着,为妥善保存和利用这些书籍,专门建经史阁,他深知这不仅是为了“士得读未见之书,人知自励”,更是为了让书籍“得为无穷之利计以永存”,确保文化载体的存续。其后,他又积极向上级(大都督府、连帅方公)陈情,“愿橅(摹印)府中所有书以归,俾学者得肄习焉”。
他的恳请得到迅速响应,府库一次就摹印赐予县学985卷典籍。经过抢救、征集、建设、拓展的一系列举措,最终使同安县学经史阁藏书达1200余卷,实现了数量与质量的飞跃,为县学教育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。其系统化、可持续的管理理念,为地方文脉的传承树立了典范。
学规整顿与考核革新。首先,针对学生“晨起入学,未及日中而各已散去”的教育现象,朱熹发布《同安县谕学者》《谕诸生》等文告,指出学生之“患贫贱不得学”的物质困境与“得学不勉”的精神困境,批判科举制度下“教不素明,学不素讲”的教育弊端,呼吁学生自省。同时颁布《补试榜喻》《策试榜喻》,效法孟子“君子五教”之法中的“答问”形式,通过命题考查学生学识积淀与思辨能力,力倡“学以为己”以回归“理义养心”的学问本真。朱熹通过整顿学规,破除科举功利积弊,确立“理义养心”之根本;通过构建“答问策论”之体式进行考核革新,以“破立并举”的双轨模式,重构了同安地方教育生态。
开新立讲、兴思辨之风。面对科举积习下学子“唯务利禄”、学问沦为敲门砖的顽疾,朱熹创立定期讲学制度,亲撰《讲座铭》立于学堂,赋予讲学仪式感。朱熹亲自教授《论语》,“诲之以义理之学而不徒为科举之文”,引导学子追求学问根本。更可贵的是,朱熹讲学重视师生互动,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记载他曾开宗明义告诉学生:“有疑焉则问,问之弗得,弗措也。”即鼓励学生大胆质疑,培养探究精神。朱熹强调:“诸君第因先儒之说以逆圣人之所志,孜孜焉。蚤夜以精思,退而考诸日用,必将有以自得之,而以幸教熹也。”即鼓励学生以勤思为基,以实践为验,以自得为归,以交流为用,形成“学—行—悟—传”的动态循环学习模式,这是教学上的革命性突破。朱熹开创的讲学新风,使当地学风为之大振,“由是邑人士知所向风,而一时道化人文于是为盛矣”。
本土精神坐标之塑造。针对同安地方“士风凋敝,后生晚学不复讲闻前贤风节学问源流”的困境,朱熹深知,空洞的说教不如榜样人物的感召。他将目光投向了同安本地人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楷模——北宋宰相苏颂(1020—1101年)。苏颂为官50余年,政绩斐然,同时亦是杰出的天文学家、天文机械制造家及药物学家,是一位站在时代前沿的巨匠。朱熹曾赞誉其“道学渊深,履行纯固,天下学士大夫之所宗仰”。朱熹巧妙利用县学旁空地,设立先贤祠,将苏颂纳入学宫祭祀体系。要求“岁时奉祀,以建遗烈使学者有所兴起”,旨在借助地方先贤的榜样效应,激发当地居民的文化自信与归属感,使同安学子得以“学有榜样”,以具象化的本土精神坐标强化地域文化认同,使之成为塑造社会共同价值的文化力量,也为后世利用乡贤文化进行教化树立了典范。
纵观朱熹在同安的兴学实践,其核心在以县学为“社会教化中枢”,构建起“空间—资源—制度—教学—礼俗”的五维改革模式。具体为:一、空间重构,理念赋形。建立符号象征体系,将教育理念融入斋名之中,使原本破败紊乱的学宫转变为承载价值符号的育人空间;二、资源整合,文脉存续。从抢救书籍到广泛征集典籍、建立图书管理制度,推动同安地方由文化荒漠走向知识共同体建构;三、立规订制,破旧立新。通过颁布学规、革新考核机制、创新教学形式等扭转科举功利导向,推动教育目标向“为己之学”转变;四、创新教学,格物致知。以互动讲学为核心,重建讲学的神圣性与求知的本真;五、礼教融合。通过树立地方精神坐标,引导当地民俗从失序状态走向礼俗规范重建。
同安县学的实践证明,教育思想绝非抽象产物,而是在回应现实教育问题中锻造出来的智慧。朱熹在同安播撒的理学种子,结出了“君子所过者化”的成果,同安由此跃升为“闽学开宗之地”,赢得了“海滨邹鲁”的美誉。同安县学的办学实践与教学经验,使朱熹意识到教育对地域文化的塑造力量,最终通过书院这一实践路径使“同安经验”转变为“书院制度”。
(作者单位:福州大学至诚学院)
扫码关注中国福建微信

扫一扫在手机上查看当前页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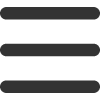


 闽政通APP
闽政通APP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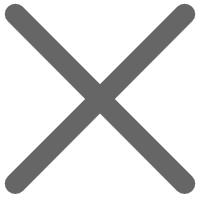

 闽公网安备:35000899002
闽公网安备:35000899002 


